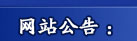《魏嵋传》前言和楔子
类别:刘沂生 作者:guanli 日期:2016-05-31 21:41:31
前 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为此,党员的素质,不但关乎党的命运,同时也关乎国家的命运,不可轻处。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某些党员的身上,也泥沙俱下,助长了一些不良习气,或贪污受贿,或包养二奶,或背离群众,竟达人神共愤,党纪国法难容之境地,直接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形象与安危。故而,对党员进行“保持先进性”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党员的先进性,当数为国为民,甘于奉献。在这方面,山东省青州东圣水村的魏嵋父子,就是光辉的典范。只可惜,因为诸多的历史原因,缺少对其了解和宣传,故令其生荣死淹,长期被历史抹煞,被人们冷落。社会发展至今日,有必要还历史一个公正,以令烈士含笑于九泉。
历史已经证明,东圣水村的魏嵋老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革命者,特殊功臣。他不但是益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山东共产党初创期的不少会议,都是在魏嵋家里召开的。相当年已有“北李南陈中圣水”、“红色的耶路撒冷”之说,岂不可作为而今我辈的学习榜样?从前的魏嵋,尚能做到“家败子孙亡,唯求国泰安”,而今的我辈,又做得怎样?彼已成为建国、建党之英雄,我辈岂可做损国、损党之狗熊!倘若深思,岂不汗颜。为此,本着陈云同志“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精神,鄙人特日夜笔耕,撰就《魏嵋传》,权为陈老百年诞辰之微薄献礼,呈献于诸读者面前,以求读后有所思,并有所得,进而有所为。
鄙人自幼好文,独钟明朝文豪冯梦龙文体,对其运用尚感自如,常用其体式撰写传奇文章,颇受读者欢迎。魏嵋的事迹,至今罕为人知,的确具有传奇色彩。本作,以传奇体式,文学笔法,再现历史真实,还历史一个公正。以传奇体式撰写党史人物,尚属一种尝试,成功与否,且留待读者品评。
我文既然为传奇文学,它不仅要以事服人,尚须以情感人。文章依据青州研究魏嵋的老党史工作者刘传功所供之有关党史资料及魏嵋重孙魏强、魏国顺所提供之家史撰就,重大史实可靠,具体细节当有加工。情之所至,行文如倾,洋洋十余万言,一挥而就,一气呵成。“浪为水波,言为心声”,文内亦有鄙人所发之感慨。对此,读者是否赞同,吾人将不与争鸣。各抒己见而已,何必强求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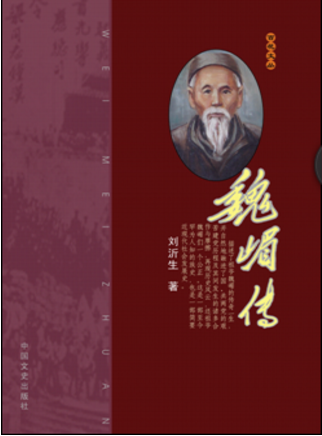 任何一个党员,都应为卫党有所付出。只有卫党,方能卫国,方能卫己。换言之,只有己清,才能国安,才得党固。己不清,党不固,国难临矣。大树若倒,何处乘荫?一叶霉烂,有损完树。信夫?
任何一个党员,都应为卫党有所付出。只有卫党,方能卫国,方能卫己。换言之,只有己清,才能国安,才得党固。己不清,党不固,国难临矣。大树若倒,何处乘荫?一叶霉烂,有损完树。信夫? 此非妄语,望君三思。仔细体味,兴许不无裨益。
我的《魏嵋传》,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族史。在撰写此章时,既不惟上,亦不惟书,因为魏嵋这个人,并不因上而生,亦非因书而存,他就是他,绝不会因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他固有的事迹和本色。为此,请你也无须拿现有的地方党史来衡量 、要求我的这部作品。
泛泛而论,历朝历代的正史,皆出自于当代御用文人之手,因受时代局限,环境左右,及作者自身偏见的影响,那些史料,虽然是可信的,却不一定俱准、皆全、通真,其篡改、隐弊、饰非、遗漏的现象实在不为少,而某些秘史、野史或家史,也不一定皆属空穴来风的臆造,其参考价值并不为小。
十年浩劫,极左路线乱中华。中华教育事业凋零,中小学教师沦落至被歧视的深渊。1977年以后,浩劫已息,虽说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教育、教师的地位并没有多大改观,广大中小学教师依然生活在被人们歧视之现实中。公元1984年9月2日,我作《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刊于《人民日报》,呼吁尊师重教。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陈云同志阅后,于9月4日作出了“尊师重教”的重要批示,颁行全国,一改极左年代那种“蔑师臭教”的恶劣局面。然而,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批示文的题目以及作者的名字。二十年后,教师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为了纪念陈云同志“尊师重教”颁布落实二十周年,我撰就出版了章回体回忆录《犟牛本色》,其中第二十六章为《鸣不平,犟牛上书感上苍 获圣批,陈老一语救老九》,专门记述“尊师重教”批示出台的始末。青州市电视台记者刘新玲对此曾经作过专题报道。然而,收到稿件的新闻单位,以“没有官方正式依据”为由,不肯给予报道。公元2005年,适值陈云百年诞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陈云》第五集时,对“尊师重教”批示的来历作了披露,始公开了这一历史史实。随即,山东《大众日报》的记者逄春阶和常诚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如果《陈云》中不公开此事,我的这一史事,人们便只能看作野史或家史,使之处于信疑参半的境地。我罗列此事,并非为宣扬自己的功绩,仅仅作为我上面论述的论据:正史与野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兴许,某些事情,野史倒比正史更为珍贵、真实。
在我们当代,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仅仅藏有一张印有孙中山先生肖像的“关金”币,也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如果藏有美金,你就会被怀疑是美国的间谍,那日子也不会好过。像魏嵋这样的人,谁肯,谁敢肯定他、宣传他?恐怕想躲还来不及呢。即使他的后裔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不敢公开其祖爷的全部历史呀!这,又有何可奇怪的呢?
山东老一代党史家陈锡德、牛瑞庭等,对魏嵋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有明确肯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刘传功与张波等,曾对魏嵋等青州老一代革命家的史料做过认真调查。他们踏遍半个中国,行程数万里,历时半年有余,掌握了许多关于魏嵋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他们人微言轻,仅是徒劳,种种因素促使这些资料束之高阁,最后付之一炬,自然也难于成史——即使承认这些史实,当时的形势,也不可能成史的。这,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国共两党,冰封对立数十载。说实在的,当我动笔撰写《魏嵋传》之初,并非一点顾虑也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伤痕,是很难抹去的。我虽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辈,惴惴之情实在难免。当我作拟至三万余字时,恰值国、共两党六十年僵局解冻,台湾国民党要人连战及宋楚瑜等应邀来访,受到国人极大欢迎,同时也引起华夏极大震动。这一政治环境的改观,为我放笔写好《魏嵋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否则,魏嵋的某些史实,我还真难落笔一书呢。即使我勇于写出,也许会招来令我穷于应付的指责吧。为此,《魏嵋传》的问世,当有连战等台湾朋友的一份功劳。
最后,有必要言明:我之撰写《魏嵋传》,仅就已经掌握的珍贵的魏嵋史料,缀连成传,让人们阅后知昔念今,誉人责己,自我清醒,自我鞭策,自我革新,以达抑恶扬善,利国益民之宏愿。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的期求。
此为题外之韵,无须多叙,言仅于此,聊以为导语。
楔 子
银行存得多多,
怀里揣得满满。
只要大权握在手,
岂怕手中无金钱。
哎呀呀,
贪赃枉法,
鬻爵卖官,
都是民脂民膏,
百姓血汗。
待到日后西归时,
怎去拜见先辈容颜?
这段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文字,因读报有感而发。
近日新闻,披露了东北某省的一件大案,从地委的书记到县里的某些领导,竟是一小撮鬻官卖爵、贪赃枉法的蠹虫,令人闻而咋舌,思而胆寒:他们,还配被称作共产党员吗?烈士浴血打下的江山落在这类人的手里,岂不可悲,可叹!

前人植树,后人乘荫,这是一般规律。不过,有些后人,不止乘荫,还在肆意砍伐巨木,极力动摇大树的根基。革命胜利了,有了职,掌了权,应该诚心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福,为繁荣中华而奋斗。然而,某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半点公仆的味道,早已变为啃咬人民的蔽虱、骑在人民头上的阎王了。这些人身居高位,不再是为民谋福,而是在为己谋财。他们的作为,与当年创业的革命者们相较,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那时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轻则献财,重则捐躯,有谁会为一己之私卖命?革命先驱彭湃,曾为革命事业,贡献上了他的全部家财,以至于自己的宝贵生命。山东省青州市的魏嵋、魏复中父子们,是辛亥革命中的佼佼者,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山东党的发起人之一,便是澎湃式的革命先驱。谁若不信,且随我回到当年去看看,也许能令你有所思。
上一篇:魏嵋传---导语及目录